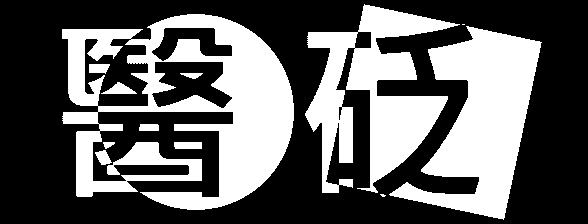| 标题 | 中国古代的“㕮咀”与“尝药” |
|---|
| 来源 | 李建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
一、
㕮咀,或作父且。丹书多见。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云:“㕮咀似以草木药茎捣碎石药。”㕮咀即制药之术语,意为捣碎。伊藤凤山《伤寒论文字考》:“盖㕮咀本必出于炼丹之法矣,遂以为诸药调合分量斟酌之名耳。今之医家调合炼药,则或有从病先尝其味,而商斟苦甘,不必如本剂分量,古人亦必然矣。”换言之,㕮咀之法晚出。伊藤氏特别提到,当时医家炼药有从病家尝味之习惯。这条线索值得留意。另,古矢刚斋《伤寒论正文复圣解》:“㕮咀,咀嚼也,取以臼杵梼碎之义也。”也有医家训㕮咀为含味,或者制药程序以口齿嚼药。众说纷纭,并无定论。
对于㕮咀的考证,新出帛简材料如马王堆《杂疗方》、武威医简皆有所见,本文将结合传世相关医书讨论;其次,笔者利用“尝药”的史料,将㕮咀源流与尝药的礼俗连系起来。以下,先从新出考古发现谈起。
二、
马王堆帛书《杂疗方》云:“●内加及约:取空垒二斗,父(㕮)且(咀),段之,□□成汁,若美醯二斗渍之。□□□□去其掌。取桃毛二升,入□中挠□。取善〔布〕二尺,渍□中,阴干,□□□□□□□布。即用,用布抿(峄)揗中身及前,举而去之。”上法涉及药布的制作。大致意思是:取空垒二斗,用口咀嚼之后,椎打成汁液。或用好醋二斗浸泡。取桃毛二斗放在里面搅拌,制成药剂。使用时取善布二尺泡在药液里,阴干。用此药布抚摩小腹部与女性阴部。帛书整理小组云,父且“其本义为用口嚼碎,后世改为捣碎,又改为细切。”主要是工具改变,切制药物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周一谋说㕮咀为后世“为制散剂之法”。此说或可商榷。㕮咀殆制药为饮片。也就是将药切制为片、丝、块、段而后煎汤饮服。事实上,㕮咀有以口含味商斟或分辨的用意。另外,以唾液 制药布,亦见于《灵枢‧寿夭刚柔》:“药熨奈何?伯高答曰:用淳酒二十升,蜀椒一升,干姜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种,皆㕮咀,渍酒中。” 㕮咀传世医籍初见于《灵枢》,与新出医帛之例相同,都是用于药熨法。上法用药四物,皆㕮咀。其中,“淳酒二十升”,此物如何“用口嚼碎”?所谓㕮咀,大约是用口尝药以后加减。《抱朴子‧登涉》辑录避毒恶诸法,“以雄黄大蒜等分合擣,带一丸如鸡子大者亦善。若己为所中者,可以此药涂疮亦愈。㕮咀赤苋汁,饮之涂之亦愈。五茄根及悬钩草葍藤,此三物皆可各单行,可以擣服其汁一二升。”以上诸法制药以“合擣”或“擣服”为主,唯“㕮咀赤苋汁”,赤苋汁一物亦无法以口嚼碎、以臼杵捣碎或以刀剉细切;㕮咀者,尝而味之,以试药之温凉寒热也。
又,武威医简“㕮咀”有数例:(1)、“治百病膏药方:蜀椒一升,付子廿果,皆父。”(2)、“治伏梁裹脓在胃肠之外方:大黄、黄芩、勺药各一两,消石二两,桂一尺,桑卑肖十四枚,怿虫三枚,凡七物皆父且,渍以淳酒五升,卒时。煮之三。”以上二例,第(1)例,张延昌、朱建平以为“父”后脱“且”字,应为“皆父且”,“意为所有药物都要捣碎或切碎”。换言之,㕮咀未必以口嚼药,如上例或有截切、锉削粉碎之工具。又,《伤寒论》的桂枝汤方,“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右五味,㕮咀。”郭霭春等注引慧琳《音义》:“㕮咀,拍呠也。”呠,为碎之误字,“旧解为口嚼如碎豆状,恐不合。”㕮咀者,此时疑是以刀切或捣、挫等制法。吴谦《订正伤寒论注》卷十七云:“凡言剉如麻豆大者,与㕮咀同意。夫㕮咀,古之制也。古人无铁刀,以口咬细,令如麻豆,为相药煎之,使药水清,饮于肠中,则易升易散。今人以刀剉如麻豆大,此㕮咀之易成也。”㕮咀的意义如上所说已有了变化。
从唐宋医家对“㕮咀”的讨论可见其变化的轨迹。唐‧苏敬《新修本草》云:“谨按:㕮咀正谓商量斟酌之,余皆理外生情尔。”宋‧唐慎微《证类本草》云:“凡汤酒膏药,旧方皆云㕮咀者,谓秤毕捣之如大豆,又使吹去细末,此于事殊不允当;药有易碎、难碎,多末、少末,秤两则不复均平,今皆细切之,较略令如㕮咀者。乃得无末,而又粒片调和也。”㕮咀之训,虽无定论,但大部份医家把㕮咀视为修药的“细切”之法,应是主流。王孝涛《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将炮制方法分为净制、切制、炮炙三项,㕮咀属于切制之例,相关文献极多。宋‧寇宗奭《本草衍义》批评上述各说:“㕮咀两字,《唐本》注谓为商量斟酌,非也。《嘉祐》复符陶隐居说细切,亦非也。儒家以谓有含味之意,如人以口齿咀啮,虽破而不尘,但使含味耳。张仲景方多言㕮咀,其义如此。”寇氏引儒家之说,㕮咀为尝药含味,并不等于制药的“以口齿咀啮”。而后世以㕮咀为细切或商量斟酌是引申意。至于稍后,如元‧王好古《汤液本草》“㕮咀之药取汁易行经络”,把药物与经络连系起来,应该是进一步的发展。如上所述,《内经》、《抱朴子》有㕮咀淳酒或赤苋汁的用药例,含味之意疑是正诂。
三、㕮咀的本义是以口含味。这个词汇之所以转移到制药的术语,可能与伊藤凤山推测医家炼药过程有尝味之例有关。
《论语‧乡党篇》载季康子送药给孔子,孔子以为对药性不明,“不敢尝”。但君亲有疾,臣、子尝药。马伯英说:“尝药为防药物中毒,特别是投毒者,保护皇上和父母辈,在当时似无可厚非。”除了防毒的理由之外,尝药别有礼仪性格,以及实际用药需要二方面的意义。
尝药较早的史料见于《左传》。《左传》昭公19年,“夏,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根据服虔的说法:“公疾未瘳,而止进药,虽尝而不由医而卒”。另外,刘向《新序》则以为“太子止自责不尝药”,但问题不在请医而在不先尝药,因此把父亲毒死,故国史书“弑”。万斯大《学春秋随笔》则推测:“夫疟非必死之疾,治疟无立毙之剂。今药出自止,饮之即卒,是有心毒杀之也。”毫无疑问,尝药旨在防毒。
《春秋繁露‧玉杯》云:“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苏舆《义证》云:“礼,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宋律有诸医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见伊川〈上谢帅师直书〉。)今律沿明律,凡合和御药误不依对证本方,及封题错误,经手医人杖一百,料理拣误不精者,杖六十。又煎调御药 ,俟熟,分为二器,其一器御医先尝,次院判,次近臣,其一器进御。皆缘《春秋》遗意。”尝药有“礼”与“律”两方面内涵。所谓的“礼”,例如《礼记‧曲礼下》:“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也表达了对医者用药的不信任。又,《礼记‧文王世子》有“疾之药,必亲尝之”。可见侍疾尝药还是孝子侍疾必行之仪式。至于尝药成为定制,汉代已有明文。《续汉书‧礼仪志》:“不豫,太医令丞将医入,就进所宜药。尝药监、近臣中常侍、小黄门皆先尝药,过量十二。”又,《续汉书‧百官志》:“章、和以下,中官稍广,加尝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别作监,皆六百 石,宦者为之”。
尝药之礼,有时不一定实施在父子之间。《汉书‧王莽传》言莽侍奉其伯父王凤以君父之礼,“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 。”因此,有父疾而子不侍疾尝药之例,则易受人议论。《史记‧五宗世家》载,常山宪山舜病,“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辄归舍。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病。”不侍疾尝药成了宪王死后,别人控告太子勃的罪名之一。后世赋予尝药一种礼仪的神圣性,亦即,父子、君臣透过此仪式而产生一体感,如北魏贾散骑之墓志有云:“侍疾尝药,同痛疡于一体;进膳奉殚,共虚饱于五内。”又,晋王澹、王沈、王昶〈母非罪被出父亡后改葬议〉一文:“亡母少修妇道,事慈姑二十馀年,不幸久寝笃疾,会东郡君初到官而李夫人亡。是时亡母所苦困剧,不任临丧。东郡君自痛远不得尝药,而妇宜亲侍疾而不得临终,手书责遣,载病大归,遂至殒亡。”王母因遗疾,不任理丧而被出。由上引文可见,侍疾尝药为孝子侍亲之所当备。这种观念大概是深入人心了。
其次,尝药还有药用上实际的功能,即为了避免医配药“不如本方”。所以,侍疾者以口含味判断药方是否对证,或随证变化而有加减。尝药不只是含味已制成之药,而是制药调合的过程有含味之惯例。中国医学史载先民对药物的了解,即从神农尝百草 的传说开始。陈莹中《张济传》云:“药王药上为世良医,尝草木金石名数凡十万八千,悉知酢咸淡甘辛等味,故从味因悟入,益知今医家别药口味者古矣。”神农尝百草,亦是以口含味。“本草”之名,或与神农㕮咀百草的传说有关。
㕮咀者,源于医者别药口味。而由含味成为制药切制的代名词。尝药礼俗,孝子于炼药过程尝而味之,以知药之温凉寒热,进而成为一种仪式行为。李杲说,古无铁刃,故以口咬药,并不正确。
四、
本文旨在考释“㕮咀”一词的流变史。结论有三:第一、㕮咀本义为以口含味。炮制药物意涵下的嚼碎、锉碎、切细等,是后起之义,《广韵‧八语》:“㕮咀、收咀,脩药也。” 大约是后人引申。第二、以口含味与尝药礼俗有关。尝药除了礼仪性的象征之外,也有别药口味之用意。第三、㕮咀或尝药,不是因古人制药工具不精、度量不确,而是医家尝味,以意分量斟酌。一如作菜调羹,厨师以口含味,不完全依照食谱原有的本剂分量。中医“五味”的知识,或与饮食经验有关。药学内史的研究,结合礼俗背景的探讨,也许是医学史研究今后应该尝试的新方向吧。
后记:本文先后承蒙宋光宇教授、李家浩教授、颜世铉教授、周凤五教授、廖育群教授、杜正胜教授等指正,谨志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