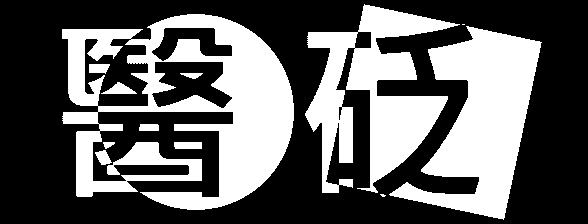晋代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作为我国针灸史上第一部专著,包含了相当多的难病针灸的内容。它不仅对《内经》作了补充的完善,在某些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其首先表现在针灸所治难病范围的扩大上。这有二种情况,一种是增加了不少《内经》中未见提及的病症。如内科补充了阴萎不用、男子失精、瘿瘤等,五官科补充了“青盲,远视不明,承光主之”、“白膜覆珠,瞳子无所见,解溪主之”(《针灸甲乙经‧卷十二》)以及鼻息肉,“鼻中,息肉不利…龈交主之”(《针灸甲乙经‧卷十二》)等。特别是妇科疾病,为《内经》所缺如,《针灸甲乙经‧卷十二》中多处提到治疗妇人绝子(不孕症)和阴挺的灸刺取穴之法。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在《内经》中被认为难以治疗的病症,《针灸甲乙经》则列为可治。如消渴一症,《内经》只提出“热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药”(《素问‧腹中论》),在《针灸甲乙经》中则列出多条据症选穴之法,如“消渴身热,面赤黄,意舍主之”,“消渴嗜饮,承浆主之”(《针灸甲乙经‧卷十一》)等。
其次,在难病针灸辨治上,《针灸甲乙经》较之《内经》更细致具体。《内经》辨症,十分粗略,《针灸甲乙经》则较为精细,如耳聋,《内经》仅分“聋而不痛”和“聋而痛”(《灵枢‧杂病》)二类,《针灸甲乙经》则分“耳聋鸣,头颔痛,耳门主之”(《针灸甲乙经‧卷十二》)等十余条之多。在取穴配方上,《针灸甲乙经》有很大的发展。《内经》一般多取经治疗,极少提到用穴,颇为笼统,《针灸甲乙经》不仅均具体记载主治腧穴,不少还提供多穴组成的针灸方。如“痿厥,身体不仁,手足偏小。先取京骨,后取中封、绝骨,皆泻之”(《针灸甲乙经‧卷十》),其中,不仅提供腧穴组方,针刺先后,还标明补泻之法。
通过《针灸甲乙经》的努力,进一步奠定了针灸治疗难病的基础。隋唐时期是针灸治疗难病临床实践进一步扩大的时期。自先秦到晋初,以针刺为主,而从东晋到隋唐,灸法得到普遍应用,故灸治难病有了很大发展。在针灸治疗的难病病种上,较《针灸甲乙经》又有增补,如内科的面肌抽搐、皮肤科的白癜风、疣及儿科的小儿遗尿等,多采用灸法治疗。如“疣目,著艾炷疣目上,灸之三壮,即除”。(《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三》)。此法至今仍有人应用而取效。为提高灸治效果,还创用了一些独特的灸治方法。如以隔物灸治瘰疬,采用“疕生商陆根捻作饼子如钱大,厚三分,安漏上,以艾灸上,饼干易之,灸三四升艾,差”(《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三》)。另用苇筒灸治耳聋,方法是先将一些药末塞耳中,然后“以苇筒长二寸内耳孔,裹四畔,以面塞,勿令气出。以面薄饼子,裹筒头以艾灸上”(《外台秘要‧卷二十二》)。近年来,有人据此法改进,称苇管灸,治疗面神经麻痹等症有一定效果。
隋唐时期,还发现了一些对难病有独特效果的奇穴,如小儿尿床,“垂两手两髀上尽指头上有陷处,灸七壮;又灸脐下横文七壮”(《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一》)。“灸左右手中指节去延外宛中三壮”(《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三》)治疗白癜风,以及症瘕,“灸内踝后宛宛中”(《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一》)等等。其中一些穴位,虽在后世已归入经穴。但是,上述穴位,目前尚未见到应用于这类疾病,其确切疗效如何,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验证。隋唐时期虽重视灸法,但如孙思邈这一类著名医家,也并不偏废针法,如治疗面肌痉挛,明确指出:“视眼不正,口斜目瞤,面动叶叶然…皆针承泣…入二分半,得气即泻。忌灸”(《千金翼方‧卷二十七》)。表明选用针刺或艾灸,须视病症而定。对有些症情严重难愈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复杂针刺手法的应用:“肤翳白膜覆瞳人…皆针睛明,入一分半,留三呼,泻五吸,冷者先补后泻复补之”(《千金翼方‧卷二十七》)。只是这类记述不多。
至唐代,针灸临床经验的积累已经相当丰富,通过长期的实践,对有些难病的针灸治疗效果开始作出符合当时水平的评价。除了针灸可治的难病外,还存在下列三种情况:一是不适宜于针灸治疗的,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指出:“凡肉瘤勿治,治则杀人”;二是同一类病症中,有适宜针灸的,有不适宜的,应作具体分析。三是即使是同一病症,针灸治疗也是分阶段性。消渴一症,孙思邈记载了六个灸治之方,表明早期治疗是有效的,但他又强调:“凡消渴病经百日以上者,不得灸刺。灸刺则于疮上漏脓水不歇,遂致痈疽,羸瘦而死”(《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一》)。这可能与重症糖尿病人易发生感染,而古代针具消毒不严有关,说明是有临床教训的。当然,王焘认为本病“灸刺特不相宜”,所以在《外台秘要》中“特不录灸刺”,则显得有些因噎废食了。以上表明,隋唐时期随着临床实践的增加,对针灸治疗难病的认识而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