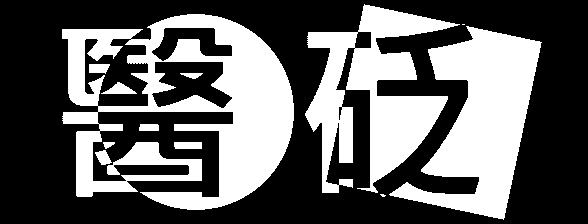沈药子 于 1999年4月
近日读到史怀哲的一段话语令我感触良深,史氏曰:“一个人与耶稣的真正关系,就是为耶稣所拥有。基督徒的一切虔敬行为,只有在舍弃自己的意志而听从耶稣的意志这一层意义上才有价值。”又曰:“对于服从耶稣的人,无论贤者或愚者,在跟他共同经历和平、劳役、奋斗和苦难的过程,耶稣便会揭露自己的真面目,于是他们将领悟到'祂是谁'这一个说不出的秘密...。”
对于史怀哲,从前只有一个印象,就是“一个肯牺牲自己照亮别人的大人物”,这个印象一直保持着,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疑问,若说要博爱,当个悬壶济世的良医,医药费少收一些则可,又何必远离亲友,将自己放逐到蛋不生鸟的阿非利加洲大半辈子、老死于斯?而类似其行径的其实又何止史怀哲一人呢?不过是以史氏作为典范。这些问题就这样摆了十多年,而何为“耶稣”?何谓“耶稣的意志”?又何以得“舍弃个人的意志”?这些都是问题。直到现在(又多虚长了十多岁)脑袋里又多塞了些东西之后,方才蕴酿出了颠覆了过去认知的全新意义。
初读到“舍弃自己的意志而听从耶稣的意志”等话语之时,便联想到王阳明的“去人欲,存天理”。明朝有个王阳明,他的论点与上述史怀哲的话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王阳明为了大学的一句“格物致知”的真义而忐忑不安,记得国中时代的国文课本内有这么一段解释,格物致知也者,乃“穷究一切事物的道理,求致立身处世的原则。”这是朱熹学派的说法,朱子治学严谨,学富五车,因此这种结论由他或其门人提出倒也不令人意外,且此说俨然已成正统。然而,约在朱子之后300年的王阳明硬是觉得这种主流的说法大有问题,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怠矣。”“怠”就是累死了,人在有生之年怎么可能“穷究一切事物的道理”之后才能“求致立身处世的原则”呢?这种依文解义的方式,实在不能令王阳明信服,于是他另谋出路,自己想办法搞它个明白,王阳明35岁因上书仗义直言而入狱,37岁谪官至龙场,在那个鸟不生蛋的蛮夷之地过了三年清苦的日子,那段时日刚好供他左思右想、肯切反省,他甚至为自己弄了一副石棺躺在其中,打算想不出来就准备死在里面了。某夜突然想通了,高兴的从石棺里蹦了出来,曰:格物,非格外在世界的“物”,乃格心中的“物”,致知,非致知识的“知”,乃在致“良知”──也就是那廓然无私的“天理”。
史怀哲的奉献私我以及王阳明为道忘身的坚持又让我联想到了悉达多太子当初舍家求道的历程,年轻的悉达多因为内心的不安与迷惑,决定舍弃骄妻、爱子、与王位,在29岁某夜溜跑出皇宫,然后遍寻全印度的明师,最后发现那些明师的教法都不够究竟,于是一个人在伽耶山的森林里苦思、修了六年,结果搞的皮包骨、营养不良,最后在菩提树下也发了毒誓,不悟道就坐死在那里算了,不起来了。结果还好让他想通了、弄懂了,而提出了缘起法则与幻我的思想。佛陀并没有以个人从蒙昧、虚幻的自我中究竟解脱为终,反而将自己的下半辈子奉献给茫茫群生。佛陀奉献的精神遂演变出后期大乘佛学的菩萨道及觉性思想。从以上三位圣哲的联想当中,我突然领悟到了某种相关性、共通点,兹先将要点略述如下:
| 个人的意志←→人欲←→无明 |
| 上帝的意志←→天理(良知)←→觉性 |
不同时空、不同圣哲的表象、使用的词汇虽不同,但其本质却有着相当的共通性,史怀哲选择彻底地将自己外放,远离他所熟悉的社会、人群,来到非洲,其行动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佛陀或王阳明,其动机何在?若单单仅是想“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单纯的博爱,若仅是如此,除了深刻的宗教信仰之外,我实在无法想像与认可,然而,史氏是个绝顶聪明之人物(他有四个博士头衔),这样的人决计无法满足于单纯的“信仰”──徒信一些教条,了无新义。所以肯定是(此处大胆假设),史怀哲有所悟道,他悟到什么呢?就是私我意志的偏跛、蒙昧所导致的一切错误行为及苦恼,以及灭除私我之后生命中本有具然的神性──也就是上帝的意志、也就是良知、也就是灭除幻我之蒙昧的清明觉性──的展现,而他更将所领悟到的化为实际的行动,到非洲实地试炼他的体悟,也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若仅是知道,不过知识尔,没有运用的知识决计不会生出任何力量。
大乘佛教好言人人皆有“觉性”,换成王阳明的术语就是人人皆有“良知”,换作史怀哲的术语就是人人皆可禀承“上帝的意志”,而无论是佛性、良知、亦或是上帝的意志,皆为人欲、无明(或说是个人的意志)所蒙蔽,唯有在澈底舍弃人欲、幻我(或说是个人的意志),它的光明才会清楚地显现,也唯有到那个时候,那个人才将“领悟到'耶稣(觉性、或天理)'是谁这一个说不出的秘密...”。王阳明认为,当遮蔽良知的人欲去除怠尽之时,便能自觉本份定位之所在,从而所言、所行皆是天理、皆自然符合道德仁义礼智信,而不须另外再立一个仁、立一个义、立一个礼、立一个智。悉达多太子从“幻我”的体悟出发,彻底领悟到我之所以为我,乃在于无始以来的蒙昧(佛家术语曰无明),行者检视内心泛起的种种蒙昧,并练习将之化解,消除人我与天地之间的隔阂,终于与天地精神冥合,成为天地之耳目、上帝的代理人、人间的明灯,尽本份内之事。史怀哲在38岁那年踏上非洲兰巴伦时,土人的鼓声传达的是:“白人巫医来了。”当他1965年以90岁高龄病逝非洲时,鼓声传达的是:“我们的父亲死了。”佛陀去逝时,他的弟子感叹曰:“世间的明灯灭了。”像这类人上人,私欲的成份已尽,肉体活着的时候便得安隐、喜乐、及苦的止息,或许也因为在人身上有此“神验”,故可推知天地或也有情,但得靠人自己去发掘。
许多人见到了史氏的博爱,佛陀的渡化众生,便以为有为者亦若斯,只见到光荣的表象,却可能忽略一个最根本的技术性问题,那就是──须先有自身的解脱,方能令他人解脱。所以佛陀曾告戒他的弟子:“己缚未解,欲解他缚者,无有是处。”而何谓解缚?就是澈底脱离人世中一切忧悲苦恼的技术。要如何办到呢?在中国有位老子,他认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于是便从忘我去体验,从忘却私我与天地的隔阂,进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然而,忘我却不是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仍有些许东西会留着,甩不掉的,那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去人欲存天理”的天理、史氏的“舍弃自我意志,听从耶稣的意志”的耶稣的意志、也就是悉达多在大败(内心)群魔、除去私我的蒙昧之后剩余的清明觉性,也就是大乘佛学所谓的去芜存菁之后的清明的宇宙识。
何以东、西方圣哲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空间,却皆能得到相似的结论?《金刚经‧无得无说分》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悟到的东西相似,却有程度上的差别,何以如此?其根本的解答或许正因为一切苦痛、烦恼的根源皆在有“我”。《中阿含‧箭喻品》曰:“有人身中毒箭不急于救治,反逼问箭是谁发的?从哪个方向射来?箭身由何种木制的?箭上的毛采自何种鸟类?则这人在还没得到答案之前就要亡失了性命。”当代人类解决烦恼的模式亦同此人,皆是本末倒置。“我”就是那枝毒箭。归溯本源,从源头截断,把毒箭拔除,以一劳永逸。“幻我”是个透过理性辩证而得到的结论,它的原理并不难,但碍于生命生而本具的对于“我”的坚固执持,却又难以融入生命中予以验证。许多人更认为,我之所以为我,此乃天经地义之事,无有深究的必要。焉知,天地之间,宇宙之中,每件事、物皆有它的原因、皆有它的道理,岂有天经地义之说?不过是习以为常,便认为天经地义尔,妄觉以为有我亦同。然而此课题对于多数人并不容易以三、两句话语打发,能否做到“忘我”也是技术性问题,故本文亦不打算深入,只是点出一个事实,就是忘我与快乐的关联。
明显的,极苦或极乐经常源于忘我。像是欣赏精采的节目看的出神,大口啖食甘美的食物、旁若无人,或沉迷于某种游戏之中而到无法自拔,或借由狂饮酒精、吸毒以臻忘我等等,但此种忘我却是耗散式的忘我,注意力向外追逐、驰骋式的忘我,人欲获得满足式的忘我,持续地耗散自身的能量。然而,一切私欲皆无满时,如同破漏的杯子,怎样也装不满,如舔刀上蜜,早晚会割伤自己舌头,虽能获得一时的解放,却会造成许许多多的后遗症,其结果经常更加苦恼。
另有一种非耗散式的忘我,注意力向内的技巧,借由否定“实我”的概念达到内心因为驰骋、追逐不舍所招至的种种苦恼的止息。基本上可归于两类,其一是透过精神的锻炼,以非耗散的方式达到忘我,如禅定、坐忘,但这个技术性较高,且须肉体与心灵相互配合,在污染严重的当代,人体普遍含毒、体质脆弱,故不太容易达到。另一是澈底的施舍,将身、心交付给群众,以渐渐臻于忘我,如史怀哲、大乘佛教之辈便是如此,相较下,此法较适合当代的环境及体质。兹将三种忘我之乐摘要如下:
| 忘我之乐 | ┬ | 不悟道 | → | 纵欲的满足 | → | 有后遗症,如破漏的杯子 |
| └ | 悟道 | ┬ | 锻炼心志以忘身 | → | 泯除私我,与天地精神 (上帝) 相应 | |
| └ | 将自我澈底施舍出 |
因此,人欲的满足与泯除私我两者所获得的快乐与苦恼,熟轻熟重,心中略为盘算即知,明眼人绝计不会逞一时之快而招来无穷的苦恼。而无论是透过四禅八定、坐忘所达到的忘我,亦或是澈底的放舍,将身、心交付给群众,以渐渐臻于忘我,不过是两条道路,殊途同归。所以,从个体的解脱的观点而言,行善或不行善已是其次,能从蒙昧中获致解放,不再受一己潜在的无明所左右,方是究极的解脱。
无论在任何时空,都可发掘出的永恒不变的道理,那个就称作真理。无论是东方、西方、过去、现在、未来,在3500年前古印度的悉达多是如此,在中国的老子、王阳明是如此,在本世纪初的史怀哲亦是如此。在佛教界一直存在着南、北传佛学之争,之所以争,乃在根本教义的差异,即如同基督与天主两教的差别,寻常人是分别不出其间差异的。然而,在考量其解缚模式与存在的意义上,觉性、上帝、良知、天理,皆是同一玄真,多种面貌,真理不灭,超越宗教的藩篱,与宇宙常存。
大乘佛教认为,生命皆有觉性,只是被私我的人欲蒙蔽了。又曰,在所谓的天、阿修罗、人、畜生、恶鬼、地狱六道之中,唯有人有机会证得正觉,因为太苦、太乐都令人无心反省,唯有苦乐参半的“人”方能思考、反省,方能推寻解缚的真理之所在,人之所以为“人”的可贵之处便在此。其实,六道已在人世之间。有些人披着人皮在行阿修罗或畜生之事,有些人虽称为人,却时时得忍受着地狱的酷刑,有些人,得天独厚,却无病呻吟。同一个人,有时活在梦魇当中,有时如同身处天界,又有时想法连畜牲都不如。人,无时无刻不在六道轮回当中循环。有些宗教认为死后有天堂或地狱,其道理也不脱六道,活着的时候便在轮回、便在天堂或地狱。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一切圣哲的本怀大抵希望在活着的时候便要解脱苦恼。
在这世纪的交界时刻,人口呈几何级数成长,为当代许多环境、资源等问题的首要根源,但控制人口成长的结果又使得人口老化,似乎两边都不是,这就是人智的侷限,解决一个问题,却制造另一个问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有些国家贫穷,有些富裕,贫穷者无能为力,甚或发生动乱,富裕的国家却还要更多,不肯施舍,滥用武力,为富不仁。由此便可看出,物质科技虽进步,人群心中的蒙昧并没有进化,甚至蒙昧加重,走向退化。
笔者曾怀疑,在人类的历史中,精神文明的巅峰其实已曾发生过、且也已经随着物质文明的发达而落幕了。目前在台湾的宗教看似发达,不过反应了人群内心的空洞与不安,而是否如此便真能明了创教者的本怀,这是个大疑问。很显然,过去因为物质不发达,所以智者都往内心开发,现代刚好相反,物质太发达了,聪明人都往物质方面开发,反而荒废了心灵的开展。然而,在当代物理学发现的事实是,精神与物质同为能量的两种变现,两者也实为构成生命个体、社会、乃至国家的一体两面,若依中国哲学传统象征性取象的逻辑,物质文明属阴,精神文明属阳,《易经》有云:“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阴阳之说乃在描述宇宙间种种现象的对立又统一的奇妙联系,阴阳若未能相调合,甚或只偏重一方,则生病变,乃至灭亡。
神魔之争持续著,